被兩個女性同時愛著,往往會培育男性自私的優越感。
在對愛情及婚姻的考慮中,凝聚的社會因素太多了。人類很難在不遠的未來實現那種完全擺脫經濟、政治等實際利益的考慮,完全從兩性相愛出發的婚姻。
過去台灣曾於1998年接受評議,當時被判定為與美國醫學院的評鑑作業標準不相當。為策動台灣改革醫學教育與建立評鑑制度,台灣因此在2000年成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於2002年再次接受評議,終獲得「相當」的認可,2009年再獲第2度認可,今年為第3度認可。
愛情也是一個追求過程,也有它的刺激力。追求的目標一旦達到了,過程結束了,熱情可能就消失了。女孩會發現,那個人並不像原來想像得那麼可愛
商品推薦: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
從男男情感和身體欲望為主的同性戀,到社會角色和氣質展現為主的男性建構,加上以革命情操和救國大業為主的國族打造,在許維賢精闢的歷史文學分析中編織成繁複而明確的軌跡,也寫出了「同志」概念在中國風起雲湧的時代氛圍中所形成的重要凝聚意義。──何春蕤,台灣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專任教授
###adout_insert###
男人選擇女友(或情人)與選擇妻子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女人是男人平靜的港灣,是男人的出發點和歸宿。
同樣是一公分的腫瘤,長在哪裡就有不同的預後,不同的人生,神就算再愛世人,也無法阻止病痛發生。病榻邊,兩個國中大小的孩子、流淚的妻子,每天守在癌症末期的病人旁,其實他們應該比醫護人員更能預期這天的到來吧?當病人因為病危自動離院時,我一直在想怎麼跟他們說再見,雖然我們不會「再見」(除非是回院開立死亡證明書)。不過我仍趁著他們收行李時,對家屬說「辛苦了,回去一路平安」,跟病人說「你辛苦了」,病人回說「謝謝你們的幫忙」,我說「沒有」,然後跟孩子說「要加油喔」。其實作為住院醫師,根本幫不上什麼忙。病人是科內討論過的末期個案,也許醫師們必須要想,從罹病到臨終的這些日子也算病人多賺到的人生吧?也許這樣才能繼續工作下去,但我卻無法很好地將客體的疾病跟人的主體分開。某次,一位臨終的病人在病房,需要醫師宣告死亡,但這位老病人的主治醫師一時抽不開身,無法前來,便指示主責的專科護理師(簡稱專師)記錄病人於下午五點死亡,但那位專師仍麻煩我協助宣告病人死亡,「因為只有醫師才能宣(告死亡)」。但在此之前,我和那位病人素昧平生,我不知道他因什麼疾病住院,甚至連名字都不曉得。和專師一起,突兀地走進三、四位家屬圍繞的病床邊,護理師已經準備好一張EKG monitor(心律監測器)印出來的記錄紙,上面呈現水平的一直線。我看了看,摸了病人的右手腕,確認沒有脈搏,忘了確認呼吸,就拿了筆燈確認病人的瞳孔反射;撐開病人的眼皮,那眼珠就像前人描述般,黃白混濁,完全不可能發現瞳孔收縮。隨後我冷靜看了床頭牌的病人姓名,轉過頭對家屬們說:「病人○○○,於2017年○月○日○點○○分於本院死亡」。和流著淚說謝謝的家屬點頭致意後,像做錯事的孩子一般,夾著尾巴逃走,我害怕家屬繼續再多說什麼,那些眼淚我承受不起,我只是臨危授命來插花的路人,但此種情景在醫院裡似乎也是見怪不怪。這次經驗,讓我回想起在血液腫瘤科實習,已經忘記住院醫師為何請我去確認病人的什麼東西。當時那位病人已經被宣告死亡,且床邊沒有看護或家屬,我帶著害怕去看病人,印象中他/她已經沒有體溫,皮膚散發出黃疸的顏色和氣味,那時我到底把病人當作是人還是屍體,其實也記不太清。只記得那時體會到一件事,「啊,原來人死後是這樣子啊」。夜間值班經常交班到已經簽署DNR(放棄急救同意書),或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的病人,同時被告知隨時有「院宣」的可能(也就是不留一口氣回家)。但從醫學院到醫院,除了被提醒應如何填寫死亡診斷書外,從來沒有人指導過或和我討論如何在病床邊宣告病人死亡。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在《臨終者的孤寂》中說:「今日只有病院裡制度化的例行公事,才為臨終處境提供了一個社會性的形態。可是這些例行公事乃是不帶感情的,而且還是臨終者之所以孤寂的重要原因。」延長生命是西方現代醫學知識體系的核心,死亡則是被壓抑、被推遲的,所以我們平常不討論死亡,不討論瀕死的過程,只剩專業不帶感情的死亡宣告。記憶同樣深刻的,是一位於病房接受安寧共同照護的末期病人,抱怨天旋地轉的症狀,我在床邊問說「那我們開止暈的藥給你好嗎?」那時病人已有發聲困難,說不清楚,於是我和看護提議讓病人用寫的看看,結果病人寫道「頭暈,但一下子就消了」,搖頭表示不用開藥。我才意識到病人雖然是末期,雖然可能因各種因素難以口語表達,但只要病人聽力正常,不代表我們就不用跟他溝通。而過去的我就常忽略衰弱但意識清醒的病人,下意識地優先和床邊容易對話的家屬溝通。之後,經過一個週末,回到醫院發現這病人已陷入昏迷,由於癌細胞轉移,病人醒來的機會渺茫,上週的紙筆溝通就是最後一次了。有時候,醫師不是在學習醫學,而是學習死亡。大概要先見識到醫療的極限在哪,看過病人在醫院最終的慘況,再來談安寧照護、公共衛生,比較不會讓人覺得空泛。因為自己才會了解就算住院治療也不一定比較「好」,而是要討論不同脈絡下,對病人「好」的作法為何。作為臨床新手,寫下這些是為了未來的自己,因為我們總是不敢面對過去。當有天變得對死亡「漠然」時,至少會被過去的自己提醒「你跟以前不一樣了」,不論那個變化是好是壞。臨床工作常逼得醫師學習淡漠,冷靜評估眼前病人,區別主觀病痛與客觀的疾病本身,略過病人的主觀經驗,以撐過充滿壓力的時刻。醫師學習死亡,但不該是學習漠然,也許關於死亡、關於病痛經驗,我們還有更多需要學習。(中國時報)
男人們則拿她與自己的妻子作比較,雖然並不自覺。
教育部表示,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被評定為「相當」的認可,顯示我國醫學教育人才培育獲得肯定,有助於醫學生物人才出國深造或考取美國醫師執照,讓留學生的學歷能與國際接軌;未來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也將申請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來檢視台灣醫學院的辦學成效及評鑑制度品質,繼續推動台灣醫學教育與國際接軌。
在內科工作的日子,有時病人會出現無法掌握的病情惡化,讓我驚覺醫療就算進展再多,新技術、新藥就算療效多好,人就是可以昨天還好好的,今天就意識不清或病危出院。同時,頻繁入院、出院的日常,讓醫病雙方以為住院都一定有出院的一天,若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有一天就沒料到再也出不了院。醫護人員應該都希望病人能出院,但病情需要時,也能熟練、敏感地事先詢問家屬:「要在院內宣告死亡?留一口氣回家?或是『形式上』留一口氣回家?」主治醫師每天平順的查房、治療,病人也都慢慢康復並出院,看似是住院的日常,不過這真的不是常態,而是運氣好的奇蹟。什麼叫藥石罔效,就是當你做什麼都不對,病人看起來越來越憔悴,然後生命徵象就開始往下掉了。高齡者有時久病纏身,醫病都較能接受大勢已去,倘若病人還年輕呢?
本書重新考掘被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大敘述遮蔽的同志書寫(1849年至2001年),反思以父權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近現代中國男性建構如何支配中國的同志書寫和性別政治。本書指出曾經作為中國性愛藝術的「豔史」傳統敘事癖好,發展到近現代中國是如何被民族國家以「性科學」為名的「性史」病理敘事機制所邊緣化,而這些轉變也非常弔詭地正是與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男性建構並肩同行,並以民族國家男性建構的「同志」之名進行連結和互相詢喚。本書重新想像「同志」的系譜,解構中國民族主義的男性建構,並提出以「『老同志』-新同志」範式來描述那些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或「社會性」論述的理論基礎上有所差異的不同男性建構表現。本書的分析對象主要是選取那些在中國大陸以男同性戀、「哥兒」或「兄弟」情誼或其他性/別議題作為敘事主軸的同志書寫,除了大量的舊報刊史料,其餘是自敘傳、私函、日記、筆記、小說、散文和詩詞,也包含從小說改編的同志電影、網路小說以及現有同志論述和反同志論述的再解讀。
名人推薦
鄭至航
真愛橋創辦人鄭至航Stark
拒絕愛情而又保持友誼,這對於任何一個被愛慕的女性來講,都是最複雜的外交藝術。
有些女孩在戀愛時,大概不光是愛那個人,更主要的是在愛自己的愛情。
一份非常具有重大價值的文獻記錄。──韓依薇(Ari Larissa Heinrich),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副教授
有人以為志同道合便是愛情,其實,愛情不僅是事業上的一致。
人往往是先愛了,才問為什麼的;可只有問了為什麼,才知道該愛到什麼程度,該不該一心一意去愛。
(2)愛情是什麼?
愛情是相互吸引,是相互刺激,是相互需要,是相互補充,是相互滿足,是相互折磨。愛情還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異性間最複雜的關係。
讓女人喜歡上你首先得臉皮厚,有些女孩嘴上說不喜歡臉皮厚的,其實她們就是最容易被臉皮厚打動的人,此類方法耗時較長,所以男生選擇此方法時要三思。其次就是用心,真心去追女孩做的事說的話才更有效果。
確定
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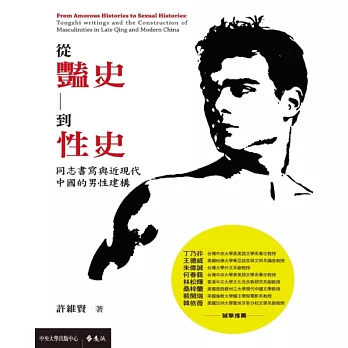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